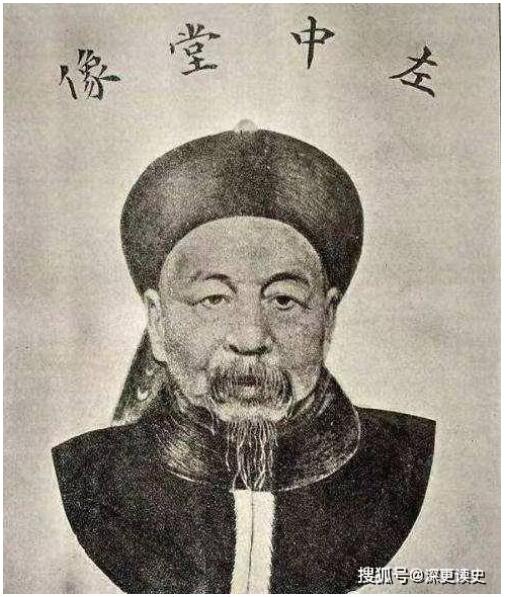芦花飞舞的季节
芦花飞舞的季节
贠靖
时令到了八九月间,河滩里的芦苇已呈现出一片透亮的金黄,那毛茸茸的芦苇花,远看似一片雪白,近看却有着不同的颜色。有奶白色的,微红色的,还有淡青色的。一阵微风吹来,细碎如棉絮的芦苇花,便在阳光下隐隐地摇荡着,放眼望去,如白色的波浪在闪烁。这个时候,整个村子便都浮在一片银白里。
这是泾河滩上最美的季节,但四妞却没有心思欣赏这美丽的风光。她刚从大坝工地上回来,那里正急需一批养护混凝土的物资。
四妞是去工地上给小山西送鞋垫的,走了半天的山路,到了那儿也没顾得上歇口气儿,就挽起袖子,过去帮着师傅蒸馒头。她在家里可是很少蒸馒头的,家里大小的活儿,爹娘很少让她插手。她们总说:穷养儿子,富养闺女。好像她是用泥做的,一碰就会倒了。
吃午饭的时候,大伙都夸四妞蒸的馒头暄白,用有一掰,一层一层的,吃到嘴里有一股子麦子的香味。主要还是面发的好,又不惜力气。不是有那么句话么:“哄乖的媳妇揉到的面”。
丁老黑一口气吃了四个馒头,过来盯着四妞打量了半晌,说了一句:我说姑娘,你有这手艺,干脆留下来给大伙蒸馒头吧!有人故意在一边起哄:丁老黑,上回来你还撵人家走哩,莫不是拿人的手短、吃人的嘴软,你才这样说吧?丁老黑反驳道:要说拿人的手短,你不也穿了人家做的鞋子么!大伙你一言我一语,都说四妞心眼好,人又勤快,为工地建设做了不少贡献,将来等大坝建成时,应该给她记头功!
小山西在一边听得眉开眼笑,心里像喝了槐花蜜。他也不言语,靠在一根水泥柱子上,不时抬头瞅一眼四妞。四妞心里也像喝了蜜,不时抬抬眼皮,偷偷地瞅一眼小山西。
这时,不知是谁提到了养护的事儿。丁老黑背着手煞有介事道:对了,这的确是个事儿。又说:这老天好似专跟人作对一般,几十天了一滴雨都不下。
那刚浇筑的混凝土,需要苫上稻草帘子,定期洒水进行养护。否则,暴晒在太阳底下是凝固不好的。
往年的稻草帘子都是从陕南运过来的,今年那边干旱少雨,稻草长得稀稀拉拉,又矮又茸,根本就结不了帘子。因此,工地上用的都是以前屯的草帘子,眼看就要用完了,这可如何是好?
见丁老黑一脸的愁容,四妞就随口说了一句:这有何难,我们泾河滩上到处都是芦苇,又高又密,我回去就把姐妹们动员起来,她们个个都是编席子的高手呢!
对呀,我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呢?丁老黑说:那芦席有韧劲,不光苫的面积大,还耐用。只是这么大的使用量,要辛苦你们泾河滩的姑娘们了!
小山西着急地朝四妞眨着眼,四妞没有理会。
没事的,这算什么,闲着也是闲着,这事包在我身上了!四妞一边解下围裙,一边拍着胸脯道。小山西在一边不停地催促着:快走吧,时候不早了,我骑摩托车送你回去。
一路上,四妞坐在后座上,伸手搂着小山西的腰,将脸贴在他的后背上,有一句没一句说着编席子的事儿。小山西低头骑着车,一句话也不说。四妞就用拳头捶着他:喂——我在跟你说话呢,你聋子呀!小山西被嚷急了,就
将摩托车熄了火停在路边,下来盯着四妞,胀红着脸道:谁让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逞能呢!四妞有些莫名其妙:我咋就逞能了?
哼,我一个劲冲你眨眼,还装做没瞧见!小山西喘着粗气道:就你爱逞能!
小山西,你今儿不把话给我说清楚,我还不走了!四妞的犟劲一下子又上来了,逼近了小山西,面红耳赤地嚷嚷着:什么就叫我爱逞能了?那是逞能吗?!
还说不是逞能!小山西气哼哼地扭过脸去:你知道那得多大的需求量吗?就你们几个身单力薄的小姑娘,能吃得下那么大的馍嘛!再说了,人家往年都是用稻草帘子,你突然给他换成了芦席,这工程质量要是出了问题,你担得起那个责任吗?这句话倒是把四妞给唬住了,但她仍不肯服软:我没想那么多,我就知道工地上有需要,我就得搭把手!
小山西的口气这会又软了下来,过去发动了摩托车说:这事咱不说了,走吧,我送你回去!
四妞仍在赌气,仰起头大摇大摆朝前走去,边走边说:你回吧,我不要你送!就这样,两个人一个在前头头也不回地走路,一个推着摩托车跟在后边。小山西几次要停下给四妞解释,四妞气乎乎道:我逞能,你别跟我解释,留着回去跟丁老黑他们解释!
天黑时到了村口上,四妞转过身盯着小山西:你回吧,不要再跟着我!小山西还想软缠硬磨,见四妞阴着脸,没得商量的样子,只好掉头回去。
四妞回到屋里仍生着气,她娘见她脸色不好,就问出了啥事儿。她说,没事儿,就是走累了,说着便躺下了。一会她爹过来叫她起来,说走了那么远的路,一定饿了,你娘给你熬了绿豆粥。她说,我不喝,你们喝吧。
生气归生气,工地上的事儿大。她爹一出去,四妞就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,跳下炕去找兰花、风铃儿她们商量编席子的事儿。
夜晚的河滩上凉风习习,柔软的苇絮儿像婴儿的手指一样抚摸着她们的面颊。姑娘们你一言我一语,都兴奋得不得了,说这回一定要争口气,绝对不能给泾河滩的乡亲们丢了脸,让小山西他们小瞧了。拿定了主意,她们便回去发动人,到河滩里割苇子。
水一样的月光下,人们一个个摩拳擦掌,手持镰刀,奔了河滩里去。一会儿工夫,一人多高的苇子就呼啦啦打着旋儿倒下去一大片。听说给大坝工地上编席子,大伙能来的都来了,在河滩里摆开了阵势,割苇子的割苇子,劈苇眉子的劈苇眉子,忙得热火朝天。
四妞猫腰割着苇子,身上的汗衫全湿透了黏在身上,手上也起了血泡,火辣辣地疼。她咬着牙,仍低头挥舞着镰刀。一会儿听得身后有人唤她,四妞转过身,是她爹他妈。她妈手里拿了条毛巾递给她,心疼地瞅着她:丫头,快擦擦!她接过毛巾,眼圈一热,拧过脸去,泪水混着汗水顺着脸颊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。她抬起头拢了拢耷拉下来的鬓发,觉得心里头一下子畅快多了。
劈好的苇眉子在河水里浸泡一夜,捏在手如细长的面条一样,又韧又软。这个时候就该姑娘们大显身手了。她们在河滩上一字排开了,手指飞快地拧动着,雪白的苇眉子白花花一片在头顶上晃动。
编好的席子又细又密,像织布机织的一样,摸上去又光又滑,铺满了河滩。第三天的时候,小山西骑着摩托车来了。看到铺满河滩的白花花的一片席子,他惊得目瞪口袋,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很快,小山西那张白白净净的脸上,就爬满了开心的笑容。他站在河对岸,远远地朝低头编着席子的四妞招着手。四妞装作没瞧见,继续低头编她的席子。兰花用胳膊肘撞撞她,朝河对岸努努嘴:有人在那向你招手呢!
别理他,四妞抬头窥了一眼河对岸,小声道:让他站着吧!
她的嘴角挂着一丝甜甜的笑。
大坝尚未建成,就传岀了要搬迁的讯息。一夜之间,泾河滩上便沸腾了,芦苇荡里也失去了平静,就连躲在河水深处的野鸭子都受到惊吓,扑棱棱地飞了起来。
最不能接受搬迁的就是四妞她爹和她娘。四妞她爹把大灰马牵到院子里,用梳子给大灰马梳着鬃毛,愁眉苦脸道:老伙计,你说这可咋办哩,人老几辈都住在这河滩上,如今说让搬走就得搬走呀,这还讲不讲道理了?
大灰马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语,一下一下甩着尾巴,神情忧伤地用头蹭着他的手臂。四妞她爹忍不住扭过脸去,眼睛有些湿润。
停了片刻,他抬起头问:丫头呢?她这会又跑到哪里去了?
谁晓得哩,这个不知深浅,没心没肺的死丫头,都这个时候了,心里一点也不着急,会不会又到工地上寻那个小山西去了?
四妞她娘说的没错,四妞此刻就和小山西在一起,不过还有兰花、风玲儿,她们是来打探搬迁消息的。小山西说,这事他也听说了,工地上的人都在议论,好像沿泾河滩的几个村子都得搬迁。他们说着话的时候丁老黑进来,见了四妞便有些难为情:姑娘,实在对不住了,你们为建大坝做了那么多事情,又是做鞋子,又是编芦席,没想到大坝还未建起来,你们却要背井离乡了……
没事,四妞笑笑道,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。不是有句话,树挪死,人挪活嘛,到哪儿不是过呢!她故作轻松地伸展着手臂。兰花一脸愁容道:听说搬迁的地方很远,很远到底有多远?风铃儿说:我也不晓得。她茫然地眨着眼: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,今天在这儿,明天还不知在哪呢!几句话说得大伙都有些伤感,心里不是滋味。
四妞她们回到村里的时候,四妞她爹把大灰马拴在门前的楸树上,几个人嚷嚷着要到镇上去讨个说法。四妞她爹抬高了嗓门嚷着:我就想当面问问那些当干部的,要把我们搬到什么地方去?为什么相隔不到十里地,让我们泾河滩的人搬走,月亮湾的人却不搬?
四妞说:爹,您就别去了。我们刚从大坝工地上回来,这是上边的决定,镇政府也做不了主。
移民搬迁的事在大伙的猜测、议论中逐渐变得明朗了:泾河滩的三十几户人家要整体搬迁到月亮湾去就地安置。县上已开了动员会,要求一定要把工作做细做扎实,给群众把政策讲透讲清楚,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,让每一户都高高兴兴地搬到月亮湾去。
散会后,县委书记拉着镇长的手,深情地说道:我十多年前就去过泾河滩,那里的老乡都很厚道呢,他们在河滩上一住就是几十年,突然间要搬走了,难免会有人想不通,也会有些抵触情绪,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,要将心比心,以情暖人,千万不能硬来!
镇长信心十足地向书记表态:您放心吧,我们能让泾河水改道,也一定会让泾河滩的乡亲们高高兴兴地搬到月亮湾去。书记还叮嘱镇长一件事,让他见到泾河滩的姑娘们代为问好。他说,早就听说泾河滩的姑娘了不得,和当年支前的娘子军不相上下,为大坝建设立了大功,有机会我一定要去会会她们!
书记的话传开来,让姑娘们兴奋不已。但真要离开这朝夕相处的泾河滩、芦苇荡了,她们还是有些不舍。
月亮湾的安置工作已热火朝天地动了起来,村主任庞玉明说,这是上级交给月亮湾的政治任务,千万不能大意,每户人家是什么情况,吃呀,住呀,干什么呀,还有娃娃上学的事,各方面的细节都要考虑周全了。刚从城里回来的庞建武说:叔,您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,这些事建平、笑笑他们已经在提前摸底了,保证完成任务!对了,听说泾河滩那帮姑娘个个都了不得,到时咱把她们都安排到村上的旅游公司来!庞玉明说:这是好事,你们就放手大干吧!好日子在等着你们!
四妞她爹听说要搬到月亮湾去,怕那边的人欺生,心里七上八下,还偷偷地跑过去打探了一番。返回的路上,他那颗悬着的心反倒踏实下来,还给大灰马背了一捆青草回来。
四妞她们这些天已在帮家里整理东西了,但人在屋里,心却早已飞走了。她们相约了来到河滩里洗衣服,衣服盆子原封不动放在河滩里,人却一个个不见了踪影。
姑娘们手牵着手,沿着河滩走了十几里地,这里的一切对她们来说是那样的熟悉,那样的亲切。马上要离开了,心里难免泛起一层层波澜。望着河滩上随风起伏的芦苇荡,她们说好了要再划一回船。
清亮的月光下,她们沿河滩而下,站在船头上,拨开扑面而来的芦苇,一会唱,一会喊,一会又蹲下来,伸出手去撩着清凉的河水,摸着滚动的鹅卵石,还有沙沙摇摆的芦苇。
划着划着,姑娘们停下船抱在一起哭了起来。那哭声穿过摆动的芦苇荡在水面上久久地回荡。一会她们又呵呵呵地笑了起来,那笑声中既有酸楚,也有欣喜和不安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