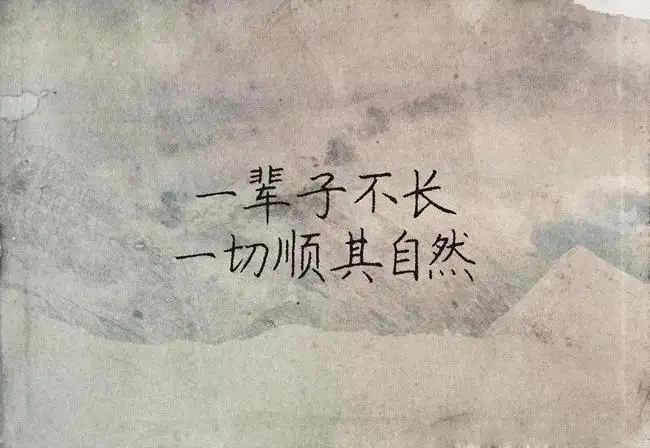来自暮年的信
来自暮年的信
亲爱的自己:
你好!
见字如晤。此刻我坐在咱家老屋的条桌旁给你写信,手边是你退役时带回来一直舍不得丢的军绿把缸,它既可以喝水也可以刷牙,内壁已积满了茶垢,像极了岁月洗不净的遗憾。春末的暖阳正透过枝叶将金箔洒在信纸上,手指抚过你此刻正疾书的同一支钢笔,墨水流淌出的字迹已不如当年那般工整,但笔触间的遒劲应当还能穿透岁月,抵达你疲惫的肩头。窗外的蝉鸣和儿时一样热闹,可我的耳朵早已听不清这些尘世间的声音了。
记得二十多年前,你总说“等忙完这阵子”,可人生无岸,生命哪有真正忙完的时刻呢?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,你总把“责任”二字烙在心上,仿佛少了你天就会塌下来。可到了我这般年纪才明白,当年熬过的夜、加过的班,不过是一叠褪了色的档案,可儿子高考前你缺席的家长会、妻子手术时你匆匆挂断的电话,父母过生日你因为出差空下的位子,却是嵌进记忆里的刺。你总担心辜负了自己的“身份”和“职业”,却忘了最不能辜负的,是那些等你回家吃饭的人。那个大雪成灾的冬天,你整天忙于巡路除雪,百姓的出行安全了,可你却中了风寒,妻子熬好的姜汤总是凉了又热、热了又凉,她在为你担心。
书架上还摆着你五十岁时熬夜赶写的稿子,墨迹早被岁月晕开,变得模糊起来,我有些伤感。可真正让我老泪纵横的,是夹在笔记本里的“合家福”,那是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合影,是你当兵走时公社干部给拍的黑白相片。那天早上村子里敲锣打鼓为你送行,父母跟在你身边一言不发,眼里却噙满不舍的泪花,父亲突然把这张照片塞到你的手里:“带着它就不会想家了”。如今他们依然健在,只是走路需要你来搀扶,说话也总是颠三倒四,唉,你当年错过的那些岁月终究是补不回来了。
你总遗憾“未能光宗耀祖”,可人生最珍贵的从来就不是功名利禄。还记得老李处长退休时拉着你喝闷酒吗?他满心感慨地说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把“副厅级”看得太重了。他现在住在干部病房里,每天盯着天花板数吊瓶里的水晶珠子,而我却能拄着拐杖去万国农贸挑最新鲜的菜,陪老父亲听评书,陪老娘认大凼边的野花。这些你眼下觉得“等有空再做”的事,在八十岁的晨昏里,都是发着光的钻石,他们嘴上说“你忙你的”“我们很好”,可你听不出那沉默里的期待吗?
你总以为透支健康是种奉献,可这副老去的躯壳正在替你偿还利息呢。右膝每逢阴雨便隐隐作痛,那是你在长白山拉练时落下的病根子;肺部总像塞着团棉絮,那是在防化演习时憋出的气管炎;这治不好的青光眼呢,都是你天天盯着电脑频幕留下的后遗症啊;还有那些年你为了应酬喝下的酒,如今都已酿成了酒精肝。此刻我多羡慕你还能在清晨疾步如风啊,还能抱起牙牙学语的小孙子亲吻他的额头。
亲爱的自己,生命就如四季流转,该抽芽时自会抽芽,当结果时必然结果,地球离了谁都还会转,可家中你却是不可替代的承重墙啊!试着在会议间隙抬头看看窗外的梧桐吧,它们不会因为少浇你那一瓢水就停止了生长。周末去中学门口接一次放学的孙子吧,他书包里装着要和你分享的蝴蝶标本。今夜就熄灭台灯,握握妻子不再柔嫩的手,那上面还留着为你做饭时切出的疤痕。
八十岁的我正替你细数光阴,每个清晨窗台上的麻雀都在提醒:生命的价值,从来不是被追逐的远方,而是此刻正在流逝的、闪着微光的当下。对了,记得这个五一假期一定要把父亲的疝气手术做了,他已经暗示过好几次,你不会又要说“等几天”吧?你口中的“等几天”可就是老人靠无助忍下的痛啊。一个一辈子不认怂的老人,你总不会等着他来求你吧。
夜已深,意难平,花未谢,茶尚温,就此搁笔。
此致。
八十岁的你于故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