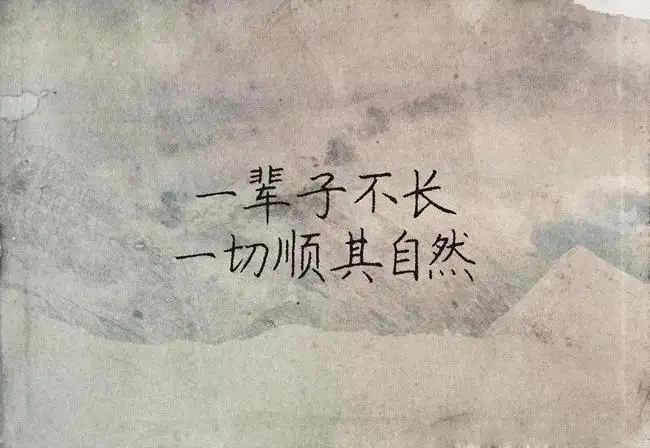五毛钱的重量
《五毛钱的重量》(纪实散文)杨崇双
五十年前的人民公社岁月,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极度匮乏,物价低廉且全国统一。火柴两分钱一盒,散装食盐七分一市斤,小楷与算术作业本六分一本,鸡蛋也不过五分一个……这些数字,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生活注脚。
1974年9月,我年满8岁,迈入了求学的课堂。学校位于诗礼公社永乐大队文波生产队地界,如今的永乐村文波社,故称文波小学。启蒙老师是一位头发花白的男老师,在他的教导下,为小学语文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二年级时是我的高光阶段,作业被老师当作示范经常给同教室的五年级学生观摩学习。一晃进入1976年9月,我升入小学三年级。从家到学校,约莫两公里的路程。在那时孩子们光着脚丫丈量路程的岁月里,这段距离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短。
三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体态微丰的年轻女老师,她既是我们的班主任,又承担着班级的全部教学任务。是九月开学初新调来的。或许是刚毕业分配至此,至于她来自哪里,那时懵懂无知的我,到现在也未能知晓。当时小学实行五年制。我们大队设有两个教学点,文波小学作为中心点,有三名老师;另有龚家小学一处教学点,则一师一校。后来另一个新村大队与永乐合并,增加了新村和务本两个教学点,仍是一师一校。中心校开设到五年级,其余教学点只办到三年级,学生到四年级就要归并到中心校就读。教室是简陋的土墙屋子,朝向室外的一面有一堵木制板墙,高度略高于课桌,却没有窗户。地面是凹凸不平的土面,桌凳残缺不全、高低不一,教室里四面透风,屋顶不漏水就算是好校舍了。每个教室有两块用木板拼接而成的黑板,一学期要用两瓶墨汁重新涂刷一遍,老师的教学工具仅有一支粉笔和一把看不清刻度的米尺。教学采用复式班模式,根据人数将两至三个年级安排在一个班级,常见的组合有一、三年级,二、四年级,或二、五年级,人数多的年级才单独成班。老师们十分辛苦,一堂四十五分钟的课,刚给一个年级讲完,就得立刻转向另一个年级授课,剩下的学生只能自行预习或复习,各年级之间难免相互干扰。作业大多在课堂上完成,课后作业很少,即便有,也不过是背诵课文、口诀之类。
这一学年,有两件事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:一件是伟人与世长辞,举国同悲,山河呜咽;另一件则与我自身紧密相关——为了五毛钱的学杂费,我险些中断学业,那段尴尬的时光,至今回想起来仍让人扎心不已。
就说说这五毛钱的故事吧。在如今,五毛钱恐怕连三五岁孩子的目光都引不来,若掉在地上或许都无人愿意弯腰拾起。但在那个年代,这五毛钱虽算不上天文数字,却足以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。那时的学校,除了课本费和学杂费,没有校服费、班费、资料费等名目。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学校如何收费,在我就读的小学,学费仅仅五毛钱,再加上语文、算术两本薄薄课本的费用。可就是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五毛钱,差点阻断了我通往书本知识的道路。
开学时,家里好不容易凑齐了课本费,再也拿不出一分钱交学费。五毛钱的学费便一直拖欠着。起初,我还怯生生地向父母问过几次,后来连提都不敢提了,生怕听到那句“那正好回来放牲口去吧”。李老师很宽容,允许我缓交。然而,随着时间一天天临近期末,那五毛钱依旧没有着落。老师大概也是无奈,开始三番五次催促我缴费。欠债还钱,本是天经地义,可她催缴的方式,却让我羞愧难当——她在教室里,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一次又一次地点我的名字,催我回家向父母要学费。一边是父母拿不出钱的为难,一头是我想上学求知的渴望,那些时日,都不敢与老师的目光相遇。每一次我的脸颊滚烫,从耳根一直烧到脖颈,小小的年纪,却承受着无地自容的窘迫,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,至今回想起来仍刻骨铭心。最后一次老师说,实在交不起,让生产队出个困难证明,可以免除。
那时,我们当地农村一日只吃两顿饭,没有吃早点的习惯。清晨,大人们忙着收拾农具,孩子们大多去放牛、砍柴、割草……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。十点左右才吃早饭,饭后便各忙各的,大人出工劳作,孩子上学读书。因为各村寨离学校远近不一,较远的有五六公里,实行半日制走读,学校一般在十一点半上课,远处的同学迟到更是习以为常。
为了这五毛钱,终于有一天,吃过早饭,我背上书包,心情却格外沉重。我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走去学校,而是鼓起勇气,朝着相反的方向,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到大约半公里外的生产队长家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求人办事,十岁的孩子独自去开困难证明,每走一步都感觉脚下虚浮,心里充满了不安与忐忑。站在队长家门口,我攥着衣角的手心浸出汗水,嘴唇嗫嚅着,半天才说出话来。队长听后,没有丝毫犹豫,翻出一页泛黄的信笺纸,在自家饭桌上快速写下几行字,签上姓名和职务,又郑重地在名字上盖上印章。一张小小的证明,就这样递到了我颤抖的手中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折好,像守护珍宝一般夹在课本里,塞进书包,然后一路小跑奔向学校。当把证明交到老师手中的那一刻,我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地,连呼吸都变得畅快起来。
五毛钱,轻若鸿毛,却在我生命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那张泛黄的证明纸早已不知所踪,但五毛钱的重量,仍在我心中留有余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