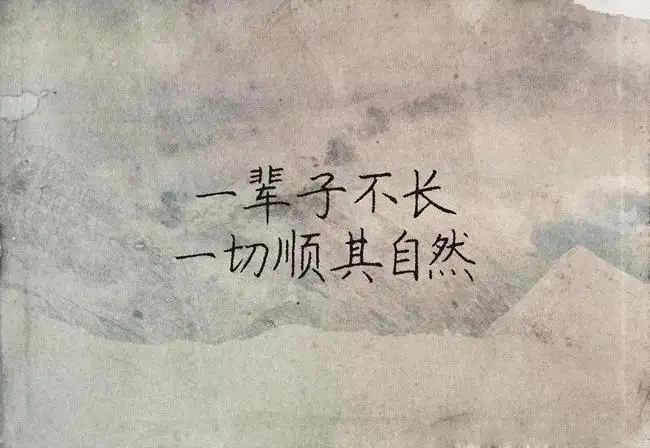自行车证记忆
自行车证记忆
整理旧物,原只为打发一个闲散的午后。证件箱里,毕业证的红、职称证的金、会员证的蓝,都妥帖地守着各自的一段人生。手指忽地触到一本硬皮小册,薄薄的,比巴掌还小些。抽出来看,封皮上“自行车执照证”几个字已褪成暧昧的灰黄色。我心里一愕:自行车,也要发证的么?
捏着这小本,指尖传来粗粝的触感。翻开时得格外小心——纸页脆了。里面用蓝黑墨水填着车主姓名、购车日期、车架号码。最惹眼的,是左下方一个印章,凸起的字迹已有些漫漶,但那郑重其事的气息,却穿透三十多年的光阴,沉沉地压在手心。我摩挲着那个印痕,耳边仿佛“咚”地一声闷响——那是当年在发证窗口,工作人员将钢印摁下时的声音。那声响里,藏着一个物资匮乏年代对“所属权”的庄严确认。
看着眼前这本蓝皮执照--那辆蓝色的“武夷”牌单车。它是九十年代初全家唯一的代步工具,更是女儿生命的第一个见证者。1991年2月17日,大年初三晚上,天寒如铁。老伴忽觉腹痛,我慌忙推出“武夷”,扶她侧坐后座。空寂的街道上,只有路灯把我们俩一车的影子拉长又缩短。我蹬得急,链盒发出急促的“嗒嗒”声,混着我粗重的喘息,在清冷的夜里格外清晰。那一刻,这辆简单的铁皮车,负载着一个家庭全部的希望与惶急。
女儿在第二天清晨来到世间。从此,“武夷”的后座便成了她的专属。我载着她穿过晨雾去上学,她在后座搂着我的腰,书包在后架上一颠一颠。铃声叮当,碾过街巷的晨昏。她学骑车也是在这辆“武夷”上,我扶着后座跟跑,看她从歪歪扭扭到能独自骑出好远,笑声洒了一路。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它被冷落了呢?城市像发酵的面团,猛地长高长胖了。道路越拓越宽,车流越来越稠。“武夷”先是在楼道积灰,后来被移到楼下杂物间。最后一次骑它是什么时候?竟一点也想不起来了。直到某天,老伴轻声问:“那旧车,送人吧?”
我们处理掉的何止是一辆旧车?我们处理掉了一种生活节奏——那种需要提前算计路途、会为半路掉链子懊恼、也会为顺风疾驰畅快的节奏。
“滴滴——”
窗外忽然传来两声脆响,短促如鸟鸣。那是一辆共享单车被扫码开启的电子音。抬眼望去,鹭岛的阳光正好,洒在那些黄白蓝绿的单车上,一片明净。女儿如今在厦门工作,我们也在鹭岛安了家。她常约我:“爸,骑车环岛去?”
我们便各自扫开一辆,沿着环岛路或筼筜湖畔悠悠地骑。海风拂面,景色如画。车轮同样转动,风景同样流过,可心情,与当年蹬着“武夷”前往医院的那份沉甸甸,终究是两重天地了。
这些共享单车,来来去去,纤尘不染。没有人会给它们打上钢印,没有人需要记住它们的号码。它们属于所有人,却不再属于任何人。
只有我手里这张小小的证,固执地证明着:曾经,有那么一辆车,它只属于一个家庭。它的每一处刮痕都知道来历,它的每一次异响都牵动心神。
我将那本自行车证,轻轻放回证件箱底层。箱盖合上,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。
时代滚滚向前。唯有那被钢印烙下的时光,和时光里相依的身影,借着这小小的纸片,在心底泛起一圈温润而怅惘的涟漪——证明曾经有一个钢印,郑重其事地烙下过一个家庭的记忆;证明曾经有一段路,必须用双脚一下一下地蹬踏,才能抵达那温暖的彼岸。
而那彼岸,如今已是一个扫码即行的时代了。
图文/晓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