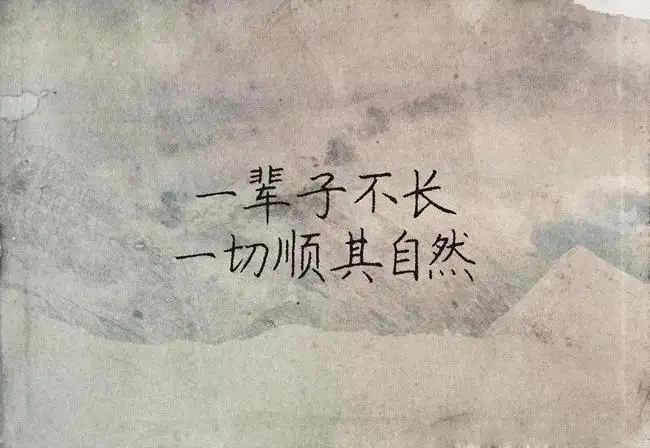雪韵祁连,心寄归途
雪韵祁连,心寄归途
编者按
雪,是北方冬日最磅礴的叙事,也是文人墨客心底最柔软的寄托。原作者孟阳以笔为镜,将祁连山的雪色、寂静与苍茫铺陈开来,字里行间满是天地相融的辽阔意境;读者清风则循着文中雪迹,以思念为线,织就一篇《炉火听雪》,让雪天的清冷与归人的温暖形成动人呼应。两篇文字一写自然之韵,一抒人心之情,于雪色中映照百态,在寂静里叩问归途,值得细细品读。
雪落祁连
——祁连山北麓的冬日独白
□孟阳
雪来的时候,万物都在梦里。
祁连山披着银盔铁甲,洪水河匍匐在冰下,整座县城包裹在厚重的寂静里。
只有风醒着,它领着雪花,沿着水井巷一路向南。
雪是决意要覆盖一切。它掩去车辙,抚平沟壑,将枯荣一并收进纯白的叙事里。土地放弃了抵抗,把舞台让给了漫天飞雪。
大朵雪绒堆满白杨的枝桠,松树则被雕成凛冽的刀锋。忽然想起岑参那句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——原来唐朝的雪,一直下到了祁连山北麓。
而真正的花,是逆风高举的鸟巢。干枝为蕊,寒雀为心,在冻僵的蓝天下保持滚烫的圆。
路旁的景观树裹着整齐的雪袄,像待检阅的士兵;唯有野草不驯服,驮着薄霜在风中起伏,呼啦啦地,把荒野的底色一寸寸还给荒野。
麻雀就在这时跃起。小黑点落在电线上,成了五线谱上颤抖的音符。风替它们翻谱,天地间响起无声的乐章——不是贝多芬的悲怆,是更古早的、属于北方的苍凉调子。
远处狗吠声撕裂雪幕,把曲子拽回人间:一声,又一声,滚烫地撞在冻土上,像在为所有远行人标注归期。
日暮苍山远,我踏上回家的路。雪光照亮前路。大地铺开纯净洁白的地毯,让人不忍心踩踏。远处有几点黄晕在飘摇——是楼上亮灯的窗,在雪夜里熬着陈年的温暖。
归途渐近,路灯温绵绵地照着,像你懒懒的眼神,光泄出来,在雪地上淌成温暖的晕。
回头望去,来路正被新雪缓慢缝合。只有那行脚印还醒着,深深浅浅,像是对大地轻声的叩问——
问雪何时停,问春何时醒,问那个踏雪归来的人,是否还认得儿时窗棂上,冰花裂开的纹路。
炉火听雪
——雪夜里的思念与归期
□清风
窗外的雪,落得让人心慌。那不是轻盈絮语,而是天地间无声的压迫,要将一切归零——连同我心底那点微弱的念想,一并掩埋。
隔着结满冰花的窗棂,祁连山的脊梁早已在风雪中隐匿,如沉默的守护者,收敛了所有锋芒。屋内静得能听见思念在血管里流动的声音。对面旧木椅空荡荡的,在昏黄灯光下,如一处无法愈合的缺口。我习惯性冲了两碗茶,腾起的热气中,仿佛看见他平日里捧碗时粗砺的指纹。可伸手一摸,只有空气的冰凉。思念具象成一缕无处安放的茶烟,袅袅散去,只留下一声轻叹。
炉火烧得再旺,也填不满满屋落寞。炭火明明灭灭,每一次爆裂的噼啪,都像在替我数着离别的时辰。我盯着火光,思绪却已翻越千山万水,去寻那个风雪中的背影。我想象路上的每一寸积雪,是否都沾染了他的温度;我想象寒风刮过他脸颊时,是否有我的目光替他遮挡。
这漫长的等待,是一种无声的熬煮。思念不似火那般热烈,它更像窗上的霜花,悄无声息地在心底结了一层又一层,凉得刺骨,又剔透得无法忽视。屋外风声呜咽,恰似离别的那个夜晚,他背起行囊时的脚步——一步一回头,把我的心也带走了半截。
老黄狗蜷在门槛旁,偶尔对外面的风雪低吠一声,又迅速把头埋进爪子。它不懂离别,只是凭着本能,守着它认定的归期。而我守着这炉火,守着这盏灯,如同守着世上最后一点念想。思念是一根看不见的线,一头系在风雪中跋涉的背影上,一头死死勒在我心口,随着风雪起伏,隐隐作痛。
忽然,门外传来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声响。
由远及近,沉闷、迟缓,却如惊雷炸响在寂静的夜里。
近了,又更近了。那不仅是雪被重压破碎的声音,更是归人叩响大地的回音。
门帘被猛地掀开,凛冽寒气裹着一个身影闯入火光。他肩头抖落一地碎玉,眉毛和胡须结满白霜。在看清那张冻得通红的脸的瞬间,积攒许久的思念决堤而出,化作眼底涌起的雾气。
他没有说话,只是静静站着,身上带着外面世界的寒冷与风尘,却以一种无比踏实的存在,填满了这个空荡荡的夜晚。
我递过一碗姜汤,指尖触到他冰凉的手。心中那根紧绷的弦,终于松了下来。
屋外的雪还在下,疯狂地企图缝合所有的路,抹去所有的痕迹;屋内的火却越烧越旺,将这方寸之间的时光,熨帖得柔软而绵长。
原来世间所有的思念,都是为了这一刻的圆满。
无论世界如何冰封雪裹,只要这盏灯亮着,这炉火旺着,那个踏雪归来的人,终会跨越山海,回到身边。